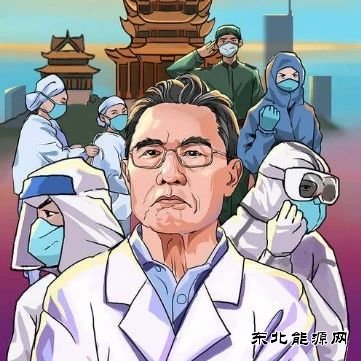沂畔秋声起,郯城处暑时
|
蝉声忽然就稀了。清晨推窗那刻,凉意裹着潮气扑过来,像刚从沂河里捞出来的绸帕,擦过后颈时还带着水痕。马陵山脚下的银杏树,叶尖偷偷黄了些,不是那种蔫头耷脑的败色,是晒足了日头的焦糖色,边儿卷着,软乎乎的。沭河边上的荷叶还撑着绿伞,就是漏下来的光更亮了——夏在郯城这处暑天里,正悄悄卸着浓妆。风一吹,有片荷叶翻了面,青灰色的叶脉清清楚楚露出来,像村口老嬷嬷撩起蓝布衫的衣角,露出磨得发亮的布边子,都是过日子的实在底色。 老县城巷口那棵老槐树,枝桠都快搭到对面墙头上了。阿婆们搬竹榻出来,蒲扇摇得“哗啦”响,嘴里念着“一场秋雨一场凉,处暑热不来”,眼睛却老往天上瞟——那片积雨云悬在那儿,她们盼着下点雨,好给自家板栗林浇浇,“今年栗子结得密,多润润才饱满”。卖吃食的担子早换了样,先前卖凉粉的老张,如今挑着芝麻糖,铜勺敲瓷碗“叮当、叮当”,把檐角打盹的狸花猫惊得蹦起来,连墙根下蜷着晒暖的老狗都抬了抬眼皮。孩子们追着蜻蜓跑过晒谷场,稻壳粘在裤脚上,一跑就掉渣。空气里飘着新米的甜香,还混着银杏果那股子说不上来的青涩味儿。最招人眼的是院墙边那丛野菊,昨天看还裹得紧紧的,今早竟开了几朵金闪闪的,跟谁随手撒了把碎星星似的,把郯城的夏末都点亮了。 走热电厂跟化肥厂家属院的路口,见着个老大娘踮着脚,伸手够路北的银杏枝。“姑娘帮我瞅着点,别折着枝桠!”她手里攥着个布袋子,摘下来的银杏叶叠得整整齐齐。我问她摘这个干啥,她笑着说:“一斤能卖七毛钱呢,攒着给小孙子买糖吃。” 指尖沾着点树胶,也不在意。 黄昏我爱往沂河边踱。芦苇荡里的白鹭“扑棱”一声飞起来,翅膀沾着夕阳的金粉,掠过水面时,搅起一串银亮的圈儿,把岸边的农家屋舍都映在水里晃。渔民收网了,船头堆着沂河鲫鱼,银闪闪的挤在一块儿。有人坐在船帮上哼郯城小调,调子被风吹得七零八落,听着竟有点像夏末的送行曲。对岸忽然亮起河灯,是晚归的村民放的,橙红的火苗在暮色里飘着,载着盼秋收的心思往下游去。有只萤火虫从芦苇丛里钻出来,绕着河灯转了三圈,好像替夏天跟这儿道别,给这夜添了点活气。 郯城的处暑,是场不慌不忙的告别。不像立秋还磨磨蹭蹭舍不得走,也不像白露急着把秋气往跟前推,就凭着日头慢慢短下去,月亮慢慢清起来,把暑气一缕缕抽走。田埂上的南瓜花还开着黄灿灿的朵儿,底下却挂着圆滚滚的小南瓜,青皮上蒙着层白霜似的粉;板栗林里的虫还在叫,就是声儿软了些,像戏快唱完了,乐手们悄悄放轻了弦。连蚊子都没了劲儿,咬个包也不红不肿,它们也知道,该给秋天腾地方了。墙根下的蟋蟀开始“唧唧” 叫,一声长一声短,像是给夏天的事儿收尾,又像在跟秋天打招呼。 北马庄村里老人忙着拾掇晒玉米的家什,竹匾、绳子搬出来,没两天,屋檐下就挂起串串金黄的玉米,跟门前银杏树的黄叶子凑在一块儿,亮眼得很。集市上,卖板栗的摊子多了,鱼鳞袋子装着带绒毛的栗子,闻着就有股山野的鲜气,路过的人都要停下来捏两个看看。孩子们最爱捡地上的银杏果,那股子怪味儿熏得人皱眉,可他们攥在手里,能把玩大半天,当个宝贝似的。 夜深了,我总爱开着窗。风从外头钻进来,带着沭河的露水凉,还掺着远处桂树没开的香,甚至能闻着田野里湿乎乎的土腥气。这风里藏着夏天没说完的话,软乎乎的;也写着秋天要开始的事儿,满是盼头。就在这淡淡的夜色里,我忽然懂了“处”字的意思——不是戛然而止,是慢慢让给新的日子,就像沂河退潮时,把光溜溜的贝壳留在沙滩上,等着下次潮水再把它们带回去。窗外的老槐树轻轻晃着枝桠,“沙沙”的响,那是郯城的季节在喘气,温柔又踏实;恍惚间,好像能听见没多久秋收时,田埂上人们的笑声,热热闹闹的。 本网通讯员:石启平 (编辑:东北亚) |

 知了集市
知了集市 小暑后,郯城似蒸笼的
小暑后,郯城似蒸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