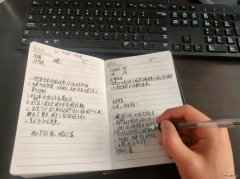晨途絮语
|
出了门,才觉出这清晨的凉意,像一层薄薄的、干净的纱,贴在脸上、手上。往大客停靠点去的路上,三三两两的,尽是上早班的职工。天色是一种将明未明的青灰色,路灯的光晕黄黄地铺开一小片,人影在里面晃着,便有些朦胧的不真实感。有的边走边吃着什么,步履匆匆,那吃食的热气在清冷的空气里呵成一团白雾,旋即又散了;有的则径直往食堂的方向去,想来是要先填饱了肚子,才有力气去队里开那班前会罢。这光景,于我这般偶尔早起的人,是新鲜的,带着一种忙碌的、属于劳动者的、坚实而又朴拙的韵律。我混在他们中间,倒像是个闲散的看客了。 抬头望时,竟见那月亮还挂着。浅浅的一痕,像一片磨薄了的、透明的冰片,不经意地贴在天幕上,了无光彩。它竟是还没有“下班”呢。日与夜的轮转,在这里仿佛有了一段交错的、重叠的余裕。我们这些地上的人,已开始了一日的奔波,而天上的它,却还留恋着昨夜的清梦,迟迟不肯隐去。这感觉颇有些奇妙,仿佛偷来了一段光阴似的。 大客终于载着我们二十余人,晃晃悠悠地出发了,向着淮南。车厢里是另一种光景。一夜的沉睡似乎还未完全从肢体里褪去,倦意便又袭了上来。靠窗的几位,已是昏昏然地闭上了眼,头随着车身的颠簸,一点一点的,像风里摇曳的稻穗。也有的,脸庞被手机屏幕的光映得发蓝,手指不停地划动着,那短促而热闹的音响——是抖音里的歌舞或笑话——便从耳机缝里丝丝缕缕地漏出来,成了这昏沉空间里一点微弱的、跳跃的节拍。我无事可做,只静静地看着窗外。田野、树木、稀疏的村舍,都还沉在黎明前最深的暗影里,只有轮廓,没有颜色,像一幅未及染墨的写意画,飞速地向后退去。世界是静默的,唯有这车轮摩擦地面的声音,单调而持续,催人欲睡。来时的那点新奇,渐渐被这漫长的、摇晃的旅途磨平了,心里空落落的,什么也没想。 一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医院体检中心,人便像一件物品,被纳入了一个精密而既定的程序里。报名,等候,再由导医领着,从一个科室流转到另一个科室。这里的一切都是洁白的,或是那种冷冷的、金属的银色,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特有的、严肃的气味。人们的话语也压得低低的,仿佛声音大了,便会惊扰了某种仪式的庄严。听诊器的冰凉触感贴在胸前,便不由得屏息凝神,仿佛在聆听自己身体内部那条隐秘的、生命的河流。这一系列的检查,像一种温柔的盘查,将平日里被我们忽略的肉身,重新检视一遍,提醒着它的存在与脆弱。这过程,竟比那一个小时的颠簸车程,更让人觉得漫长。 待到一切完毕,在医院食堂里领了那份免费的早餐——一碗温热的白粥,一个雪白的馒头,一碟清淡的小菜——坐下来慢慢地吃着时,才仿佛从那个被仪器与数据定义的世界里,重新回到了人间。肠胃被食物熨帖着,身子也渐渐暖了过来。 再登上返程的大客,情形便全然不同了。已是上午九点,真正的白昼君临天下。那轮迟迟不肯“下班”的月亮,早已不知隐退到何处去了。窗外是明晃晃的、饱满的阳光,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,给田野、房屋、乃至远处公路上奔跑的车辆,都镀上了一层鲜活的金色。车厢里也仿佛被这阳光注入了活力,来时的那种昏沉与静默,被一扫而空。大家的脸庞都明朗地亮着,话也多了起来,谈笑风生,像一锅渐渐煮开了的水。 谈得最多的,竟是孩子的上学,与家庭的收入。 “……我家那个小的,偏科得厉害,语文能考班里前几,数学却像听天书一样,真真愁死人。” “愁什么?找个好老师周末补补课就是了。如今这补课费,才真叫人发愁呢!一节课就是一张‘红票子’。” “谁说不是呢!挣得总觉着赶不上花的。盼着他考上个好大学,将来找个好工作,我们这辛苦,也算没白费。” “工作哪有那么好找?你看现在……” 这些话,琐琐碎碎,平平实实,没有半点文采,却像脚下坚实的土地,承载着生活全部的重量。孩子的分数,是悬在心头的一轮月,有圆有缺,牵动着悲喜;那或薄或厚的收入,则是每日升起的太阳,催人奔波,也给人暖意。这旅途的始与终,这月与日的交替,竟仿佛一个巧妙的隐喻了。 我们来时,披着月光,带着未醒的困倦与个体的疏离;归时,却迎着艳阳,满载着俗世的喧嚷与共同的热望。 我看着窗外流淌而过的、光辉灿烂的田野,听着耳畔这鲜活而真切的絮语,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,不知何时已被填满了。这,或许就是最寻常,也最安稳的人生光景罢。大客平稳地向前行驶,将晨露与月色甩在身后,正奔向那一片坦荡的、光明的白昼里去。 本网通讯员:张安坤 (编辑:东北亚) |

 立冬,郯城皇亭路的时
立冬,郯城皇亭路的时 我想和你去春天里坐坐
我想和你去春天里坐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