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然:月是故乡明
|
中秋的脚步,是悄悄来的。先是风里挟了一丝半缕的清甜,是糕点铺里新出炉的月饼香;而后,天色洗得愈发湛青,像一块凉润的玉;待到那夕阳的余烬彻底冷却下去,天地间便为那一轮将满未满的月,预备好了一片庄重的舞台。城里过节,终究是热闹的,却也带着几分仓促。华灯早早地亮起,与天上那轮尚显清瘦的月争着辉光。超市里,各色月饼堆成玲珑的塔,莲蓉的、五仁的、火腿的,裹着金箔银箔,在灯下闪着富丽而疏离的光。人们提着精美的礼盒,步履匆匆,那盒子里装的,似乎不单是吃食,更是一份人情,一种义务。这热闹是好的,是人间烟火的证明,只是总觉得隔了一层,像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。我的魂,却总被这月色牵着,飘回那遥远的、记忆里的故乡去了。
故乡的中秋,是从灶间开始的。祖母是那座小小王国的君主,节前好几日,她便指挥着母亲与姨娘们忙碌起来。面粉是自家麦子磨的,带着阳光的朴拙气息;馅料是最经典的芝麻花生,掺着晶亮的冰糖粒儿。我总爱蹲在门槛上看,看她们的手如何将一团团素白的面,捏成碗状,填上饱满的馅,再在模具里轻轻一磕,便落下一个个月牙白的、印着“福”“寿”花样的生坯。那光景,空气里弥漫的不是香气,而是一种踏实而温暖的期待。
最妙的,自然是庭中望月。
夜沉静下来得时候。没有街灯的搅扰,天幕是纯然深邃的蓝黑色,月亮便毫无保留地、雍容地升了上来。那是一轮怎样饱满的月呵!像一位盛装的新妇,光华四射,却又温柔敦厚。清辉如练,静静地泻下来,将屋檐、每个人的脸庞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边。
祖父会指着月里模糊的暗影,一遍遍地讲那讲了无数次的故事:“看,那是吴刚,还在砍那棵永远砍不倒的桂花树哩。”我们便仰着头,拼命地看,仿佛真能看见那寂寞的身影。而祖母则会轻声哼起那古老的歌谣:“月奶奶,明晃晃,开开大门洗衣裳……”歌声混着秋虫的唧唧,在溶溶的月色里飘散,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。
那时吃月饼,是一种庄严的仪式。供月之后,祖母会用刀将一个月饼小心翼翼地切成几等份,每人只能分得小小的一牙。捧在手里,舍不得立刻吃完,先小口地咬着那层层叠叠的酥皮,再细细地品那满口生香的馅料。那甜,不是腻的,是厚实的、醇厚的,一直能甜到心底里去,仿佛将一整片月光都吃进了肚里。
如今,我在这流光溢彩的城市阳台上,望着同一轮月。科学告诉我,月球上只有环形山与月海,没有广寒宫,没有桂花树。手里的月饼,馅料愈发新奇,包装愈发华美,却再也吃不出那一牙“福”字月饼的滋味了。
我忽然明白,我魂牵梦萦的,又何尝只是那一块月饼呢?我怀念的,是那方可以赤脚奔跑的庭院,是那阵带着草木气息的晚风,是祖父母温存的絮语,是那份将整个心都填得满满当当的、单纯的欢喜。那一切的载体,便是故乡的月。它不只悬在天上,更沉在心底。
月,自然是同一轮月。可看月的人,与看月的心境,却再也回不去了。那轮最明、最亮、最圆的月,终究是落在了那片叫做“故乡”的土地上。
(编辑:东北亚) |

 中煤新集公司安监局:
中煤新集公司安监局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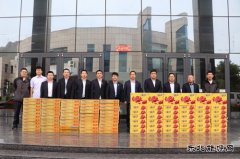 “橙”心“石”意 情
“橙”心“石”意 情 韩家湾煤炭公司:中秋
韩家湾煤炭公司:中秋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