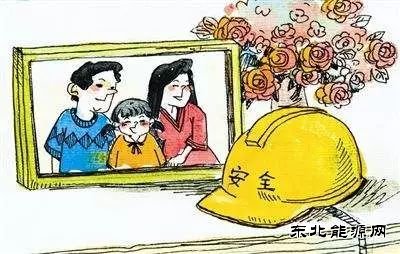双节同辉处,郯城月正圆
|
当中秋的明月刚攀上西关三街的屋檐,国庆的红绸已缠上街角的灯杆。整座郯城浸在桂花酒般的蜜色光晕里,风里都飘着暖意。老街似被施了魔法,红灯笼串成流动的星河,风拂过轻晃,影子落在沥青路上,漾开细碎的红。糖炒栗子的甜香从巷口漫出,勾得路人驻足深吸;墙根下打盹的老黄狗醒了神,尾巴摇得像拨浪鼓,鼻尖还往香气里凑。 晨露沾着墙根青苔时,西关三街的张大娘已在院里支起竹匾。她的手拢着细碎星光似的,轻轻一抖,新采的桂花簌簌落下—— 瓣瓣金黄沾着晨露,落在青瓷碗里,像撒了把月光。“这桂花得晒足三个日头才醇,前几天下雨耽误了,今儿总算晴了。”老人说着,眼角皱纹漾开笑,指尖捻起片沾灰的花瓣,小心吹净。 红绿灯旁的糕点铺,蒸笼吐着白气。五仁的醇厚裹着核桃香,枣泥的甜润沾着蜜意,两股香气在晨风中缠成软网。店前小姑娘拽着妈妈衣角,眼睛黏在橱柜的枣泥月饼上,小嘴抿成月牙:“娘,我要那个印花的,闻着好甜!” 最热闹的是老槐树下。半大孩子蹲在树影里,捡碎砖瓦片堆 “月亮塔”,塔尖插着新村广福寺求的平安符,红绳随风飘。十岁的虎子踮脚想把苹果搁塔尖,脚一滑,塔“晃了晃”要倒。卖糖画的张大哥箭步冲过去,长柄铜勺“叮”地接住苹果,没凉透的糖汁顺勺沿淌下,在阳光下拉出金闪闪的弧线。“小鬼头,塔倒了月亮可找不着家咯!” 围观人都笑,笑声惊飞槐树上的麻雀,扑棱棱往街巷里去,也想凑这份热闹。 我骑车载着风往北去,北马庄的玉米裹着金壳,在秋风里晃,叶尖沙沙声像千万面小鼓。村口老石桥栏上,几个孩子坐着捋玉米须编“月亮绳”,编好系在柳枝上,风一吹,金流苏轻晃,映得水面发亮。 “老刘家的闺女回来啦!”不知谁喊了一声,穿汉服的姑娘提竹篮走进场院。篮里苏式月饼带着油纸香,酥皮上“花好月圆” 的朱砂字红得喜庆。场院中央,八十岁的刘大爷裹着孙子的小手搓玉米粒,金黄颗粒越堆越高,成了小山丘。“爷爷,月亮为啥总跟着咱走?” 小孙子抬头,手里还攥着半粒玉米。老人望向天边渐圆的月,眼里泛着软光:“月亮记着哩,庄稼人不管走多远,心都朝着家。” 暮色漫来时,场院支起圆桌。刚炖好的羊肉汤冒着白气,膻香混着胡椒味飘得远;蒸笼一揭,花馍馍的麦香扑脸,捏出的花瓣还热乎着。李大爷举起酒碗:“今年玉米亩产破千五,全靠国家好政策!” 话音落,远处传来鞭炮声——张刚家小子考上军校,红喜报贴在院门口,烫金的字晃眼。两桩喜事凑一块儿,酒碗一碰,满村飘着酒香,连月亮都似被熏得更圆了。 最后一缕晚霞沉进马陵山,郯城成了盛月光的容器。沭河水波晃着月光,画舫慢悠悠漂,穿旗袍的姑娘倚着船舷,船头灯笼的光落进水里,碎成一河星子。岸边场院,说书人讲“嫦娥奔月”,茶客嗑着瓜子搭腔,笑声裹着故事飘远。忽然有人指天喊:“快看!月亮里有桂花树!” 众人抬头,月光下的云絮真像桂树枝丫,竟与传说重合。 郯国古城广场上,非遗师傅演“火龙钢花”。滚烫铁水往夜空一泼,“哗”地溅出金红钢花,像漫天流星坠落,映亮每张脸。穿唐装的老人抱着孙女,小姑娘问:“爷爷,月亮和钢花谁更亮?” 老人摸她的头:“月亮是老祖宗的光,照了千百年;钢花是咱今儿的劲儿,热热闹闹的。俩光凑一起,才把回家的路照得亮堂堂。” 子夜时分,我走上古城墙。月光像流水,浇在“郯国古城”的石碑上,把字缝里的灰都洗亮了。远处传来秦腔《月满西楼》,悠扬的声儿裹着月光飘远。城墙根下,年轻人举着手机直播,弹幕里飘来 “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”,字里行间的想家劲儿,隔着屏幕都能触到。 当双节的月光洒过长城与珠江,照过漠河雪原与曾母暗沙的浪花,我才懂这片土地的浪漫——从西关三街的月亮塔,到北马庄的玉米场院;从古城落满钢花的夜空,到直播间飘着唐诗的屏幕。这月光是五千年文明酿的酒,洒在每个中国人眼里,亮闪闪的:是盼团圆的暖,是庆丰收的甜,更是民族一辈辈追好日子的光。 晨光染亮沭河水时,画舫又载着游客出发了。船娘摇橹的 “呀嚯”声,与远处收割机的“突突”声慢慢合在一起。老的、新的,都裹在没散的月光里,透着熨帖的暖。我知道,等明年中秋月再攀西关三街的屋檐,这座小城又会讲新故事——关于灶台上的团圆,田埂里的丰收,还有中国人永远盼着的、更红火的日子。 本网通讯员:石启平 (编辑:东北亚) |

 布尔津执法大队:双节
布尔津执法大队:双节 国网牡丹江东宁市供电
国网牡丹江东宁市供电 国网阿鲁科尔沁旗供电
国网阿鲁科尔沁旗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