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煤陕北矿业涌鑫公司:煤的自述
|
我是一块煤,全身漆黑坚硬的煤,一般人看到都会心生厌恶,讨厌我的肤色,讨厌我的相貌,但人们可知我内心坚强,心生温暖,照亮世界。在自然界,我们煤的家族是一种特殊的存在,活跃时间之长久,生存地域之广阔,最重要的是我们煤族诞生之初是以另一种优美的姿态而存在的—高等植物。
我出生在距今大约1.5亿年的地质历史时期—侏罗纪末期,最初的我是以蕨类植物而存在。说起侏罗纪,我不得不说我们的近邻—恐龙,是的,恐龙是和我们共存的。想当年,我们的枝叶正好为恐龙提供了生存必备的美食,要不是有我们植物家族的繁荣,哪来恐龙的鼎盛。 我生长在如今称之为鄂尔多斯盆地所在区域的古森林里,当时的古地理环境很温和,气候湿润多雨,地势平坦广阔,湖泊河流广布,参天古树蔚然成林,遍布千里。当我还是一颗大树,生活在一片大森林里,旁边比我身体强壮的朋友比比皆是,我们的身体深深植根于一片湖泊边沿地带的潮间带,根紧握在地下,叶相触在云里,每当我抬起头,我就能看到湖泊远方的世界,一条小河蜿蜒延伸向远方,成批大鸟在天空盘旋,巨型野兽来了又去,接天美景碧空尽,生活别有滋味。 可是,好景不长,在我三百岁那年,突然有一天,一切都改变了。记得那天傍晚时分,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发生了剧烈的颤抖,地震致使地表下沉,沉陷最终导致湖水侵埋了我们的躯体,在被掩埋的一刹那,我最后一眼瞥见了恐龙仓皇逃窜的脚步和天边的最后一抹晚霞,最终,我还是难逃厄运,缓缓的闭上了双眼,至此我便开始了地质“演变”。 侏罗纪的谢幕,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,也是我们古生物的不幸。 在以后的几百万年间,燕山运动时刻不在伴随着我。日出日落,潮起潮伏,海陆反复变迁。我的躯体侵润在潮湿的湖水里,慢慢的,年年岁岁无穷无尽地折磨和岁岁年年永无休止的苦痛,终于有一天,我的意志被消磨殆尽,躯体渐渐被腐化成了泥炭,我伤心不已。更可怕的是那些经年被风蚀、搬运、沉积的厚达几百米的泥沙重重的倾轧着我孱弱的身体,纵便有千种苦楚,更与何人说。 在之后的百万年里,我看惯了冰冷的春风秋月,也目睹了世间的生死轮回,适应了地球的喜怒无常,也感叹于生命的短暂脆弱,一种生物走向终极,也许会有新的物种获得新生。在时光的罅隙里,在一棵草的生命里,我梦到了最初的那片森林。 时间之河迅速的向前疾驰而去。长长的夜空里,我抬起了头,紫微星划过,只眨了一眨眼,已经远离我一光年。蓦然回首之际,在一块琥珀的眼睛里,我看到了自己,时光催容颜,我已非当年!漫长的等待中,殊不知我时时刻刻都在被迫改变,我由煤族最原始的形态开始了变质:泥炭—褐煤—烟煤—无烟煤,也许是习惯了沉默与等待,或许是黑暗掠夺了我的天性,我渐渐演变成今天这幅模样,还有谁会记得我当年模样?也许,我也快忘了吧! 时间摧垮了我的身体,但却始终没有摧毁我的意志,我还有梦想,还有使命。我只是希望有重见光明回到蓝天下的那一刻,奉献我身体里的能量,即使粉身碎骨,灰飞烟灭,我也在所不惜。绵绵等待无绝期,可我还是在等。 地质历史长河奔流不息,亿万年就像是一场梦。经历种种坎坷与苦难,在新生代的全球造山运动背景下,我脚下的土地再一次被撼动,这次却是缓慢抬升,坳陷盆地变黄土高原。目睹了第四纪冰期与间冰期的轮番上演,也见识了海进海退的无聊重蹈,渐渐地,我身上的重负被风蚀搬运到了远方,命运的转轮使我距梦想越来越近。怀着跳动的心情,跟随着追逐的脚步,终于有一天,在刺眼的矿灯中,我被新一轮的地球统治者—人类带到了魂牵梦绕故土,激动兴奋已无法形容我的心情,亿年修将归故里!可是,眼前已非当年,桑田沧海,物非人也非,细流当年万里湖,森林如今却不毛。 在世间的日子里,我全面的了解如今的地球和人类,如今的第四纪孕育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与辉煌。在当今社会发展的浪潮下,煤炭被开采出来当做燃料,为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,作为煤族成员,这点我还是很自豪的。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机械声,数次中转就像是旅行,当我再次睁开眼时,我出现在了一个农家小舍,一户人家正围着火炉取暖,一家人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,小女孩脸色红润,暖洋洋地靠着母亲打盹,一旁的父亲则偶尔往火炉里加入煤块。窗外北风呼啸而过,炉内火苗欢快跳跃,看着这幅祥和温暖的画面,我的心弦不经意间有所触动,也许这就是我的使命,燃烧自己,温暖别人,当火苗在我身上肆意蔓延那一刻,我笑了…… 本网通讯员:康强伟 (编辑:东北亚) |

 蒲白建庄矿业:就地过
蒲白建庄矿业:就地过 淮北双龙矿业公司职工
淮北双龙矿业公司职工 陕煤陕北矿业涌鑫公司
陕煤陕北矿业涌鑫公司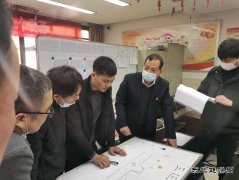 蒲白矿业煤矿运营公司
蒲白矿业煤矿运营公司


